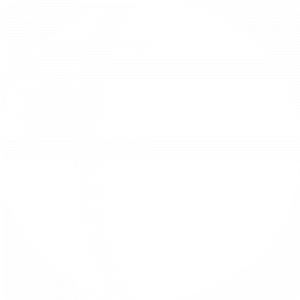是充電,也是暫停
自我日本留學歸國並正式進入職場,進入策展和美術館經營的工作直至2020年,將近滿十年。在一檔又一檔的展覽策畫永不停歇的工作輪轉中,我深刻感到自己需要「暫停一下」,讓自己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沉澱與盤點這十年來經歷的各種人事物,同時心中也悄悄地許願能夠短暫離開熟悉的環境,出走到一處陌生地。而這個想要出走的小小願望,成了2021年年底申請傅爾布萊特的契機。
出走,不只是離開,也是探索。紐約是全球博物館美術館的一級戰區,各種藝文活動集中,人文薈萃,當我在思考研究方向與對象時,紐約即成了我心中的首選。而位於多元族群和移民人口眾多的紐約皇后區的皇后美術館(Queens Museum),也成了我長久以來關注移民遷徙與離散議題的最佳目標。
另一方面,2019年底至2020年初於全球爆發的COVID-19也帶給博物館界極大衝擊,我所任職之忠泰美術館也曾於2020年與2021年兩次經歷疫情不得不閉館數月。我擔任忠泰美術館總監之職責,與團隊並肩歷經各種沙盤推演及多次館務危機處理,不時考量各種因應方案及影響面向,深感疫情對於博物館/美術館經營影響之劇烈。因此,我希望能夠實地拜訪紐約的美術館與博物館,了解這些館舍在經歷2020-2022年這長達三年的疫情衝擊與影響後,面對什麼樣的困境,並如何克服?疫後如何重建並經營團隊,以及因應危機,經營模式的改變與調整,如何規劃觀眾關係重建計畫?
疫後復甦的大都會
我在依舊寒冷的2023年3月底初春抵達紐約,在炎熱的暑假7月底回到台灣,這整整120天,親身見證了一座曾被疫情折磨殆盡的死城,再次復甦為充滿活力與觀光客的大都市。如果說,隨著季節而逐漸升溫的氣候,以及隨疫情趨緩而逐步開放是紐約官方復甦的主旋律的話,那麼在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下,曾受疫情影響深受打擊大量裁員而充滿變動的人事環境,以及延續自2020年發生的喬治·佛洛伊德之死所引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之後,讓全美對於種族問題的深層焦慮浮上檯面的社會張力,則成了我當時所身處的紐約整體環境中一個不間斷持續低鳴的背景音。
危機中的美術館:策展的創新作法,以及公眾關係策略的轉變
1. 與社區共生的皇后美術館(Queens Museum)
皇后美術館位於紐約皇后區,這是紐約多元族裔和移民聚集之處,來自南美、亞洲、中亞、非洲等各種不同地區的人聚集於此,約有一半的居民為外來移民,約有165種語言在這裡被言說。皇后美術館本身的建築在1939年和1964年,共兩次做為萬國博覽會中的紐約館建築,在1972年時正式以皇后美術館的身分再次開幕。美術館本身就位於整個博覽會公園的中心位置,其最著名的收藏便是巨大的紐約城市的全景式(panorama)模型。皇后美術館於1990年代開始,便已經是舉辦非西方主流文化的重要場館,包含日本藝術家柳幸典和中國藝術家蔡國強等,更在1999年邀請了全球重要策展人共同策畫「Global Conceptualism(全球觀念藝術展)」,奠定了皇后美術館在美術館界/藝術界致力於介紹多元文化與觀點的立場,此展獲得專業界極高評價。更因為皇后美術館所處的地區的多元文化背景,與當地居民和社區的長期合作計畫也曾結合展覽計畫當中。除了像是「The New New Yorker」計畫邀請當地居民以藝術創作的方式學習英文的活動或工作坊,更有邀請居民直接與藝術家共同創作的展覽,運用不同方式協助不同族裔的移民融入美國文化。
在2020年Covid-19疫情期間,皇后區是全美國遭受疫情影響最慘重的區域,確診死亡和患病人口佔全美確診人口的一半,此區的族群在社會經濟地位上多為弱勢。皇后美術館在疫情期間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2020年6月,紐約疫情還正處於最嚴重的階段,全民都處於封城緊戒的狀態時,皇后美術館便與當地非營利組織La Jornada 共同合作發起食物發放(Food Pantry)」的計畫,開放美術館的空間,讓民眾得以在此領取來自食物銀行等機構捐贈的免費食物,幫助這群弱勢族群度過沒有收入、缺乏食物的艱困時期。皇后美術館長期與在地社區團體合作,針對不同的文化議題進行各類的工作坊或是展示。即使在美國政府已經於2022年9月宣告疫情已經結束之後,皇后美術館仍舊維持每週進行的食物發放,及各種與在地社區合作的計畫以支持在地社區及廣大弱勢族群。
我的接待機構( Host Institute)即是皇后美術館,因此我訪問了館長與館內不同部門的館員,以及負責社區教育的藝術家,從他們的訪談當中,可以深刻感受到,美術館勞資方的緊張關係與不穩定性。加上2022年的參展藝術家公開於網路上抨擊皇后美術館對於非裔藝術家的爭議做法,並提出正式聲明,連我一位外部人士也都能感受到皇后美術館壟罩在低迷的氣氛當中。即便如此,在2023年的艱困時期,皇后美術館依舊以展覽策畫和社區教育計畫,以及持續推動食物發放,持續扮演連結社區的重要角色。



2. 勇於顛覆大師之策展手法:布魯克林美術館( Brooklyn Museum)
布魯克林美術館位於紐約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一樣,是遠離曼哈頓中心的區域,這裡也擁有多元文化的社區族群。布魯克林美術館的建築本身也經歷過幾次巨大的改造,從一開始1907年代以帕德嫩神殿(Parthenon)式的空間設計,到1940年將巨大階梯拆除改為平地入口,經歷60多年之後,於2004年再邀請建築團隊Polshek Partnership Architects重新改造美術館大廳入口空間。整個建築的改造過程,就如同將美術館民主化的過程以空間和視覺展現,讓所有民眾都能夠沒有門檻的親近和接觸藝術。這樣的入口大廳的空間規劃,以高度的開放性和透明度,體現了布魯克林美術館在博物館經營上的立場,與民眾同在,與社區同在,展開手臂迎接觀眾。
2020年5月全美疫情還處於嚴重高峰期間,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民眾抗議高峰時期,布魯克林美術館選擇與民眾站在一起,館方開放空間供抗議民眾使用,並提供各種製作海報和文宣的材料供免費使用,以表達他們與民眾站在同一陣線的態度與立場。館方甚至在經歷2020年與2021年疫情洗禮後的布魯克林更重新檢討其館藏當中的以白人歷史為主的敘事方式,改變了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畫像展示的位置。
根據布魯克林美術館社區合作部門主任Laval Bryant-Quigley在訪談中提到,2020年之後館方開始尋求更多與當地社區溝通的機會,邀請社區組織代表參與討論,了解社區的需求與文化,諮詢她/他們對於展覽的看法與意見。並具體將其需求反應在展覽內容上。我訪問她的2023年當下,布魯克林美術館正推出「A Movement in Every Direction: Legacies of the Great Migration」展覽,以當代藝術策展來討論在美國歷史上1915 年至 1970 年間發生的「大遷徙」。美國重建後時期數百萬美國黑人逃離家園,大量人口流動導致了美國人口、經濟和社會政治構成的根本轉變,展覽透過當代藝術作品來反思這段歷史,展覽中更將布魯克林作為全美大遷徙中的另一個重要地點,重點介紹了有關該行政區遷徙模式的歷史和當代人口普查數據。館方也邀請觀眾透過收集口述歷史的方式分享他們自己的個人和家庭移民故事。
Laval 更進一步分享,在2021年,當總統拜登簽署六月節(Juneteenth)為國定假日法案生效,將六月節定為紀念美國廢除奴隸制的全國性節日。此後,每年在六月這個季節中,布魯克林美術館也將全館空間開放,舉辦相關的慶祝活動,包含音樂表演,戲劇演出,在地食物市集等,讓美術館成為多元文化交流的平台。
2023年,同時也是畢卡索逝世五十周年,全球各大美術館紛紛舉辦各種和畢卡索有關的展覽,布魯克林美術館也策劃了一場別具用心的畢卡索展《It’s Pablo-matic》(取自與畢卡索名稱Pablo Picasso諧音的展覽名稱) ,美術館邀請澳洲喜劇演員漢娜·加茲比(Hannah Gadsby)策劃。加茲比曾於2018年推出的開創性喜劇特輯《娜內特(Nanette )》曾公開抨擊藝術史上一些最傑出人物的不可饒恕的行為。本展透過展場內的作品並置手法,並配上加茲比犀利幽默的語音導覽,展出了一百多件作品,其中包括畢卡索的作品,以及琪琪·史密斯(Kiki Smith)、梅·史蒂文斯(May Stevens)、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蕾妮·考克斯(Renee Cox)等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展覽不僅突顯了加茲比的觀點,也展現了許多參展藝術家的聲音,探討了圍繞厭女症、創造力、藝術史經典和「天才」等複雜議題。
同一時期,我也在曼哈頓的古根漢美術館參觀了以藍色時期為主題的畢卡索展,以十分安全保守的策展手法,不意外地吸引眾多觀光客。像這般大多數的美術館都以「天才」與「大師」來回顧畢卡索時,布魯克林美術館以顛覆的觀點重新省視與反思既定藝術史,顛覆既有敘事,讓我感到十分驚艷與敬佩!此展也是我心中年度最佳展覽的第一名!



3. 疫災中撫慰人心的魯賓博物館(Rubin Museum)
魯賓博物館位於美國紐約市曼哈頓中心區,以西藏以及喜馬拉雅之文化藝術為主題,展示藏傳佛教文物與經典物件為主的美術館,在疫情期間發展出許多撫慰心靈的策展與線上資源。以我實際參觀並訪問策展人的當時展覽為《死亡並非終點(Death Is Not the End)》。此展包含來自藏傳佛教與基督教的版畫、油畫、骨飾、唐卡、雕塑、泥金裝飾手抄本和法器等,以三大主題:「人類境況」,即我們對今世死亡的共同理解;「中間狀態」,即煉獄和中陰的概念;以及「來世(Afterlife)」,重點關注復活、轉變的理念和天堂。本展以藏傳佛教與基督教對照的方式展示,讓觀眾看到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對於人類生存與死亡與再生的不同詮釋,但卻也展現人類共通的無常處境,以及眾生對於延續生命的渴望的思考。特別是在疫情之後全球動盪、充滿失去摯愛,以及不確定性的當下,這場展覽更凸顯了一座美術館能夠為社會提供沉思與安慰的角色。
魯賓博物館更在疫情期間便已經積極推出podcast,邀請多位藏傳佛教靈性導師、腦神經研究者精神科研究者、歌手共同以「覺醒(Awaken) 」為主題,持續錄製一系列的節目,以無形的方式提供社會各種心靈的支持與撫慰,
Behind the scenes: 探究美術館幕後與自我反思
四個月紐約駐地,我進行了許多場深度專訪,訪問對象包含各大美術館/博物館館長、部門總監、資深策展人、教育人員、教學藝術家、社區推廣人員、建築類策展人、多元文化官等人。透過實地的參訪以及面對面的訪談,我觀察到許多美術館幕後工作環境/職場的文化問題,看到不同立場面對的問題,其中對我而言,最大的衝擊,就屬博物館/美術館界管理階層和基層員工的對立與衝突。不僅前述提到的皇后美術館藝術家與館方的衝突,包含費城美術館以及其他美術館,都曾發生多起發起自員工的工會抗議事件,職場因為人事異動頻仍而呈現不安的狀態。位於紐約都會區的美術館多為基金會運作,極度依賴觀光客門票及商品銷售收入、董事會的捐款,以及募款,而因為在疫情期間大量裁員而造成管理層與基層的緊張關係,持續至疫情逐步復甦的2023年。隨著博物館再次開放實體空間而不得不再次招募人手的美術館管理層,則面對更多爭取自身權益與社會正義的年輕工作者。博物館職場中,無處不見到「多元、平等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簡稱DEI)」的標語與宣導,但對照實際狀況,明顯還有許多要走的路。
紐約是資本極度集中的都會,最富裕的上東區依然聚集了弱勢的無家可歸者群,各種奢華高級的場景與各種社會衝突和危機,混合交織在紐約這個大都會。我曾在大都會美術館的大廳出席開幕典禮,體驗夢幻般的奢華酒會,觀察上流社會階層與博物館界的完美連結,在隔一天在皇后美術館目睹眾多社會弱勢和移民者大排長龍來領取免費食物。這個充滿衝突與差異,同時也充滿了機會,紐約這個大蘋果,造就了她本身無可取代的地位。
衷心感謝能獲得傅爾布萊特的訪問學者機會,在經歷120天紐約藝文界的洗禮後,我暫時遠離熟悉的環境,面對完全不同的環境,觀察了許多社會與美術館的議題,看到問題也思考了其解決之道。這段經歷讓我能更客觀回頭思考自身工作的意義與價值,是我生命中無可取代的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