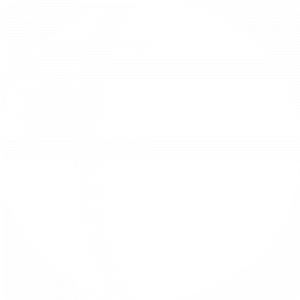劇場幕後的力量:駐美觀察與反思
筆者服務於OISTAT國際劇場組織(國際舞台美術家劇場建築師暨劇場技術師組織)長達九年,該組織是非政府國際組織,旨在促進劇場幕後工作者的國際交流。
過往工作過程中,筆者觀察到一般大眾對於劇場幕後工作的認識十分有限,因此本次計畫以「美國劇場組織如何提升劇場幕後工作者能見度」為研究主軸,於駐美期間深入了解美國劇場相關非營利組織,如何透過不同方法提升劇場幕後工作者的能見度;除了認識不同組織之外,過去筆者長期推廣國際劇場趨勢,故也藉此機會,觀察美國目前的劇場生態與發展趨勢。
歷經震盪的美國劇場社群
抵達波士頓滿一週,尚未適應寒風刺骨的嚴冬,我帶著既緊張又期待的心情,與我獎助期間的計畫導師,同時也是同時也是波士頓大學大都會學院藝術行政研究所所長的Douglas DeNatale教授會面。在簡短討論我的計畫後,Douglas告訴我,我來到美國的時間點很有趣——在疫情之後,美國的劇場產業有了劇變。
後疫情時代全球通膨飄升,本就非屬高薪工作的劇場人,除了過長工時,還得面對生活不下去的窘境。2025年1月12日,在與外百老匯大西洋劇院(Atlantic Theater Company)談判協商破裂後,劇院公會在IATSE國際戲劇舞台從業人員聯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Theatrical Stage Employees)帶領下,組織了劇場幕後工作者的罷工行動,以爭取更高的薪酬待遇。此一罷工導致正在預演場(Preview)的《悲傷營(Grief Camp)》以及《我想你認識大衛.葛林斯潘I Assume You Know David Greenspan》兩檔節目演出取消。大西洋劇院公會和經營者間的協商最終於三月份落幕,兩檔演出陸續回歸搬演。
劇場幕後工作者時常面臨龐大的生活壓力,而劇院經營者同樣也得面對經營壓力。雖然隨著解封後的觀光熱潮,劇場觀眾逐漸回流,但製作成本也因為通膨節節攀升。如何在維持劇院穩定營運與提供良好福利間取得平衡,是藝術管理人不得不面對的課題。
而另一個讓產業大震盪的消息,不外乎就是川普政府上任後,削減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平等、包容)相關政策的行政命令。身在非營利國際組織,多元、平等與包容向來是我們所堅信的價值,而劇場社群則因為處理之議題、從業者背景與自我認同等因素,讓DEI顯得更加重要。
此一行政命令尤其衝擊依賴聯邦政府資金的藝文組織。2025年2月,川普政府罷免了原本由拜登總統任命的18位甘迺迪中心董事會成員,並指派自己為董事會主席,任命政治盟友理查.格雷內爾(Richard Grenell)為臨時總裁。這一舉動象徵著聯邦藝文機構的「去專業化」與「去自治化」,引發劇場界與文化界強烈反彈。多位藝術家與文化策展人辭職抗議,甚至連甘迺迪中心原訂上演的《漢密爾頓》(Hamilton)也取消演出。川普政府同時關閉了甘迺迪中心長年支持少數族群的「文化核心」(Culture Caucus)計畫,使許多在地聲音無處發表。
與此同時,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NEA)也因執行新政面臨大規模高層出走。多位藝術領域資深管理人於2025年集體辭職,抗議機構運作遭到政治干預與價值扭曲。原先推動多元文化創作計畫的補助亦被取消。許多地方劇場因聯邦補助終止而陷入困境,像是康乃狄克州唯一的非裔加勒比劇場Pa’lante Theater便因失去6.5萬美元補助被迫停演並裁員,其他州亦有數百項計畫遭撤銷。這場補助政策轉向對美國地方藝文生態系造成沉重打擊,尤其影響了長期服務於弱勢社群的非營利劇場與文化工作者。
川普政府對甘迺迪中心與NEA的干預,加上對DEI政策的全面否定,使美國劇場產業面臨雙重挑戰:制度性的支持網絡受到破壞,同時藝術與文化實踐的價值基礎被削弱。當政治意識形態進入藝術資源分配的核心,劇場界不只要為經費奔走,更需在價值壓縮的情境下,重新思考藝術工作的意義與社會角色。
你付的票價,我們的專業
波士頓大學藝術行政研究所自2019年與倪德倫環球娛樂公司(Nederlander Worldwide Entertainment)合作,開設表演藝術及商業劇場課程,該公司是由百老匯兩大巨頭之一——倪德倫家族第三代成員Robert Nederlander, Jr所創辦,主要經營美國以外的國際市場。
在與現任執行長Bob Nederlander, Jr.訪談過程中,他問了我一句至關重要的問題:「你認為推廣幕後工作者為什麼重要?」點醒我在研究過程中最大的盲區——忘了去思考「對觀眾而言重要嗎?」身為藝術管理工作者,思考每件事背後的目的,是我的工作心法,但也許因為在目的明確、旨在建立國際交流環境的工作中許久,便逕自認為提升劇場幕後工作者的能見度,能夠讓劇場工作環境更加健全。
Bob分析道,觀眾通常不會意識到劇場幕後工作的存在,因為他們更在乎的,是舞台上眼睛所見的事物。若從商業劇場觀點出發,將票賣出去、創造營收是核心目標,而「教育」觀眾並沒有這麼重要,但觀眾若能透過推廣活動,更加理解一齣戲的複雜與劇組付出的心力,也許能夠提高他們對於劇場的忠誠度與回流意願。另一方面,若從非營利劇場的觀點出發,公益與教育本就是其功能之一,這些劇場更重視文化使命與社會責任,因此提升觀眾對劇場幕後工作的理解與認同,不只是擴大藝術參與的方式,更是回應其組織使命的具體實踐。
訪談結束,帶著「為何重要」的探問,這塊缺失的拼圖似乎也在後續資料蒐集的過程中逐漸清晰。
「我認為提升劇場幕後工作者能見度是重要的,因為這讓觀眾了解他們付的票價,都去了哪些地方。」同樣是波士頓大學商業劇場課程的講師之一,曾多年任職於紐約市立芭蕾舞團舞台管理、目前於National Dance Institute擔任製作總監的Melissa Caolo如是說。觀眾願意為演出買單,代表他們認同製作的價值;而在缺乏政府補助的美國商業劇場環境中,如何讓觀眾理解票價所反映的不只是眼前所見,而是整體製作流程中各部門的專業與勞動,更顯得格外重要。
此一觀點讓我重新思考:若觀眾能從一開始就接觸劇場、理解表演背後的複雜與專業,也許未來就更能支持這個產業,成為既有參與感、也懂得欣賞的人。然而,「現在美國高中的劇場教育比較偏重台上的表演者,讓很多人認為只有演出能力不夠好,才會去擔任幕後工作」,Melissa也點出美國劇場教育的現況。這樣的偏誤不只影響學生對幕後職位的認知,也可能在無形中削弱了觀眾對整體製作價值的理解。
假若能從教育著手,讓更多孩童在學校時期便認識劇場與幕後工作,不但能夠打開孩童對藝術的視野,同時,也將有機會培養更多潛在觀眾,以及未來劇場產業的工作夥伴。
藝術教育不可或缺
根據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EA)於2015年發布的報告《The Arts in Early Childhood: Social and Emotional Benefits of Arts Participation》,0至8歲的學齡前兒童參與音樂、戲劇和視覺藝術等活動,有助於提升其社交技巧和情緒調節能力。例如,經常參與音樂活動的幼兒表現出更高的合作能力和獨立性。此外,戲劇教育對青少年的學習和發展也具有積極影響。研究指出,參與戲劇活動的學生在學業表現、自信心、同理心和社交能力方面均有所提升。例如,參與戲劇教育的學生更有可能完成高中學業,並在大學入學率和學業成就方面表現優異。
劇場工作除了創作本身,更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合作能力、以創意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跳脫傳統框架思考的勇氣與方法。這些能力正是未來世代面對多變世界的重要素養。
為此,美國有許多倡議劇場教育的組織與計畫。例如,American Alliance for Theatre and Education(AATE)、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re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ASSITEJ)的美國會員中心TYA/USA、Association for Theatre in Higher Education(ATHE)等,都是會員制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讓兒童、青少年等不同年齡層有機會接觸到專業劇場演出與教育資源。
呈上所述,美國劇場教育在公私部門的倡議下雖然逐步普及,多數青少年與兒童對劇場的認識仍多集中於「表演」,較少有機會了解舞台背後龐大的專業分工與職涯樣貌。以百老匯聯盟(The Broadway League)推動的《Broadway Bridges》為例,該計畫提供每張十美金的低廉票價,供紐約市公立高中學生進劇場觀賞百老匯演出,藉此建立年輕觀眾與劇場的連結。雖然這樣的計畫有效拓展了藝術參與人口,讓更多學生得以踏入劇場,但他們的參與多半停留在觀賞層面。假若要從根本提升劇場素養與認同,教育應從觀賞、理解,到實作與投入,逐步建構學生對劇場全貌的認識。
在此脈絡下,紐約市非營利組織 Inside Broadway 所推動的「Creating the Magic」可視為引導小學生進入劇場世界的第一道門。該計畫透過精心設計的導覽活動,帶領學童走入百老匯劇場,在觀賞片段演出之餘,親眼見證音響、燈光、舞台機構等幕後技術的運作方式。此類以「觀演+導覽」為主的模式,有助於建立孩子對劇場工作的初步認知,降低距離感與陌生感。若「Creating the Magic」是建立孩童對劇場的第一印象,那麼《Working in the Theatre》則是一扇深入理解專業分工與職涯面貌的窗口。
美國劇院之翼(American Theatre Wing)推出的《Working in the Theatre》,長年以紀錄片形式呈現劇場各領域的專業職人,包括舞台經理、舞台技術、燈光設計、聲音設計等,讓學生在課堂或家中皆能接觸到劇場生態的全貌。該系列影片免費上架,累積觀賞次數已超過數百萬,成為許多教育工作者與非營利機構引介幕後職能的常用資源。
若希望進一步引導學生從觀察進入實作,美國劇院之翼與 Design Action 合作的「Springboard to Design」計畫,則展現出教育深度的另一種可能。該計畫鎖定有興趣探索劇場設計的高中生,提供為期一週的免費夏季密集課程,由專業設計師擔任導師,課程涵蓋舞台、服裝、燈光、音效與投影設計,學生將與專業設計師學習設計思維並實踐創作。此類實作導向計畫不僅能激發學生興趣,也有助於引導其思考劇場職涯的可能。
整體而言,從 Inside Broadway 的導覽式體驗、Working in the Theatre 的知識性紀錄,再到 Springboard to Design 的實作課程,三者展現出劇場教育由淺入深的可能路徑。若能串聯不同階段的教育資源與合作模式,將有助於完善劇場教育的生態系,讓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能走進劇場、了解劇場、進而成為劇場的一份子。
新銳從業者的進修機會與人脈連結:從教育延伸到職場過渡
當然,劇場教育不應止步於學生時期,對於剛踏入職場的新銳從業者而言,持續學習與拓展人脈在競爭激烈的職場環境格外重要。在美國亦有許多為了新進設計師與技術工作者設計的進修機會,協助新鮮人累積實務經驗並建立專業網絡。OISTAT美國會員中心USITT美國技術劇場協會即為搭建劇場幕後工作者的交流平台,每年舉辦年會則有許多教育性質活動,供新銳劇場人連結人脈及進修。
其中,由 USITT 發展的 The National Design Portfolio Review (NDPR) 是設計領域的重要平台。該活動通常於紐約舉行,開放給舞台、燈光、服裝、聲音、投影等劇場設計畢業生與初階從業者,提供與業界專業人士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參與者除了能展示作品集,還能獲得職涯建議與聘用可能,許多知名劇場或設計團隊亦會派代表出席,尋找新興人才。
另一個指標性活動是 Hemsley Lighting Portfolio Review,專為燈光設計新銳所設,紀念已故設計師 Gilbert Hemsley。該計畫由一群致力於人才培育的資深燈光設計師主辦,邀請甄選後的參與者在紐約展示個人作品,並與業界領袖一對一面談,接受指導、建立人脈,也常是進入專業設計圈的起點。


除了上述活動,教育機構也積極介入職涯銜接領域。Studio School of Design 是由波士頓大學燈光設計主任 Mark Stanley 與燈光設計師 Clifton Taylor 所創立的非營利教育機構,專注於實務導向的設計訓練與多元社群支持。其課程涵蓋舞台、燈光與聲音設計等領域,並以可負擔與高品質並行為宗旨,致力讓各種背景的新銳從業者皆能持續學習、拓展實務技能。
以華盛頓特區的 Studio Theatre 為例,其「Studio Theatre Apprenticeship Program」長年以來提供劇場設計、舞台管理、製作等多元領域的全職實習職缺。參與者不僅能在專業環境中接受密集訓練,還有機會參與實際製作,並與劇場內部團隊深度互動。該計畫強調跨部門合作,讓新銳人才能理解整體製作流程、訓練職場軟實力,是許多年輕設計師進入職場前的重要跳板。
這些以技術與設計為主的實習與作品審查制度,不僅是知識延伸的機會,更構成進入劇場產業、拓展人脈、累積實務經驗的關鍵橋梁。它們讓剛從學校畢業的新銳從業者,在劇場專業的真實環境中磨練技術與溝通能力,為正式踏入職場做好準備。
從劇場獎項看出產業趨勢
在這些進修與實習機會之外,劇場產業本身的評價與肯定機制,也對從業者的職涯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獲獎紀錄往往成為設計師與技術人員建立聲望與擴展職涯機會的重要資產。透過觀察美國劇場相關獎項的設計與評選標準,亦能一窺當代劇場產業如何看待幕後工作者的價值與角色變化。為了解美國如何透過劇場相關獎項表彰劇場從業人員,筆者在獎助期間試圖蒐集美國所有劇場獎項的相關資訊,然而過程中碰到的最大挑戰,便是獎項資訊相當不透明。
美國劇場獎項繁多,較為人所知的包括東尼獎(The Tony Awards)、戲劇桌獎(Drama Desk Awards)、外圈劇評人獎(Outer Critics Circle Awards)等全國性獎項。除此之外,針對不同職業類別、地區、劇場規模等尚有許多其他獎項,例如由波士頓劇評人協會(Boston Theater Critics Association)主辦的Elliott Norton Awards,即是波士頓在地最具代表性的劇場獎項。另一例則是芝加哥的Joseph Jefferson Awards(簡稱Jeff Awards),長期評選該城市專業與非專業劇場的創作成果。
針對獎項資訊,自1945年起出版的《Theatre World》雜誌曾詳實蒐錄各類美國劇場獎項,但隨著該雜誌停刊,目前尚無一套完整的統整資源。許多獎項網站僅公告當屆得獎名單,對於評選標準、提名機制、甚至歷年資料並不公開,也缺乏完整資料庫可供查詢,造成研究與理解的困難。
本次筆者約蒐集到40個劇場相關獎項,其中多數仍以百老匯與外百老匯製作為主。這些獎項的評選方式多由藝評人組成的委員會負責,少數則邀請專業工會代表與業內人士共同參與。例如Drama Desk Awards即由劇評人、編輯、出版人等所組成的Drama Desk成員投票決定,而Elliott Norton Awards則由新英格蘭地區的資深劇評人投票選出。雖然評選機制大致仰賴專業意見,但較少見到系統性的公開標準,也未必重視所有技術職類的平等曝光。
值得一提的是,成立於1965年、由American Theatre Wing協助主辦的Henry Hewes Design Awards,是美國第一個將百老匯、外百老匯以及外外百老匯(Off-Off Broadway)放在一起評選的劇場設計獎項。此獎前身曾名為Maharam Awards,主要由劇評人Henry Hewes推動,長期致力於提升設計工作在劇場藝術中的地位。Henry Hewes Design Awards早期僅設有舞台設計、服裝設計與燈光設計三項主要類別,其他如音效、投影等設計元素皆被歸在「傑出特效」(Notable Effects)一類之中,直到2020年才正式將聲音設計與多媒體設計獨立出來,設立專屬獎項。
這一轉變反映了劇場產業對聲音設計與媒體科技專業的重新認識與重視。此趨勢亦與近年來劇場技術快速演進、沉浸式體驗日益普及有關,也使得更多跨領域與技術背景的設計師有機會被看見。由此可見,劇場獎項制度不僅是一套表彰機制,也形塑著整體產業對專業價值的理解與未來發展方向。
另一個近年備受矚目的趨勢,則是演員獎項中性別分類的調整。傳統上,大多數劇場獎項皆以「最佳男主角」與「最佳女主角」等分類方式頒獎,然而隨著對性別認同與非二元性別(non-binary)的理解提升,部分獎項已開始移除性別分類,改採中性命名。例如外圈劇評人獎(Outer Critics Circle Awards)自2023年起取消男女演員分類,統一以「最佳主要演員」(Outstanding Lead Performer)稱之。羅特獎(Lucille Lortel Awards)也於2022年宣布取消所有性別區分的表演類獎項,強調每位表演者應該以表現實力而非性別認同為評斷標準。
這些變革不僅回應劇場社群對多元性別與平等參與的重視,也再次凸顯劇場作為文化前鋒的角色。獎項制度因此成為產業價值觀轉變的重要風向球,從設計專業的擴增到性別制度的鬆動,皆反映了當代劇場對包容性、公平性與多元表現的積極回應。
追尋我們的文化
三個月的獎助時間說長不長,好似在稍微蒐集完備背景知識後就得返台。雖然還有許多資訊值得更深入的挖掘,但駐美期間除了研究主題外,更有許多經歷讓我反思劇場如何成為一種文化與價值的體現——不只是台前幕後的產業運作,更是我們如何理解自我、訴說歷史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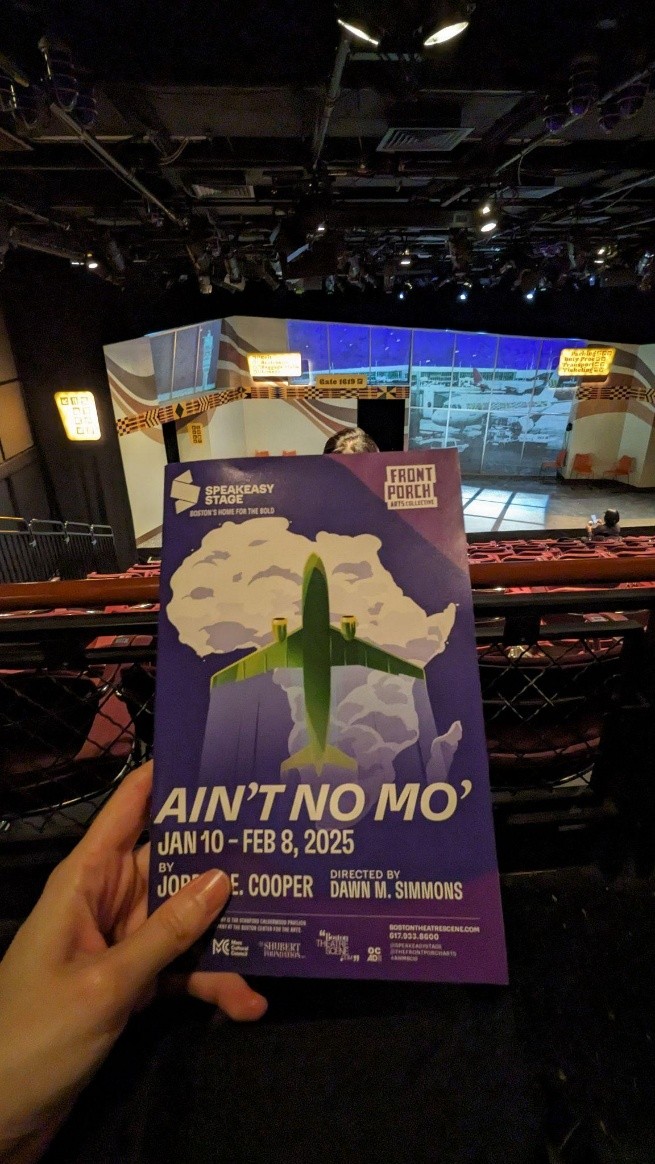
我在進駐期間於波士頓藝術中心(Boston Center for the Arts)觀賞了《Ain’t No Mo》以及《The Grove》兩檔演出。《Ain’t No Mo》曾於2022年登上百老匯舞台,卻因票房不佳僅上演六週便草草收場。該劇以一個虛構但震撼的假設作為開場:「如果美國政府送給每位非裔美國人一張單程機票回到『家鄉』,你會怎麼做?」透過幾則荒誕卻寫實的片段,深入剖析種族歧視、歸屬與認同的難題。《The Grove》則是以身體與聲音為媒介,呈現一段有關非裔女性祖輩的集體記憶與精神連結,讓我深刻感受到,劇場作為一種社會實踐,不只是再現現實,更能建構一種療癒與對話的空間。
這些作品不約而同地訴說著族群經驗、歷史創傷與對於未來的想像,而其之所以能夠誕生、演出、與觀眾交流的背後,正是因為美國劇場在制度上長年投注資源於多元聲音的發掘與呈現。從DEI政策的推動、藝術補助的資源配置、劇場教育與觀眾培養的制度設計,到對幕後工作者的肯定與獎勵,這一切都不只是為了產業發展,更反映了「文化」在一個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反觀台灣,我們或許也需重新思考,在追尋自己文化的過程中,劇場扮演著什麼角色?我們是否給予足夠的支持讓多元聲音被聽見?我們是否建立了健全的制度去照顧那些無法站上鎂光燈的工作者?而在一場場演出、一個個創作的背後,我們是否真正看見,那些關於族群、性別、階級、與土地的集體記憶與未竟之夢?
獎助雖短,但讓我更堅信文化政策與劇場制度的設計,絕不只是行政或預算上的議題,而是關乎我們如何面對彼此、理解彼此,以及共築一個更有尊嚴與創造力的社會。這次的經驗是一個起點,也是一份提醒——我們要更有意識地尋找、珍視與說出我們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