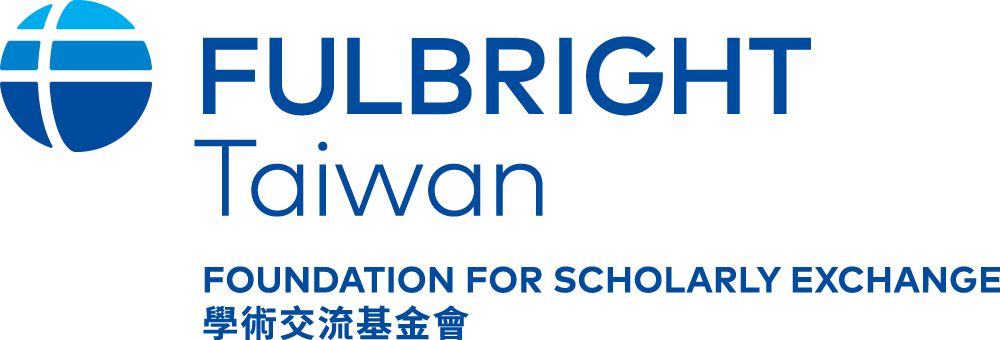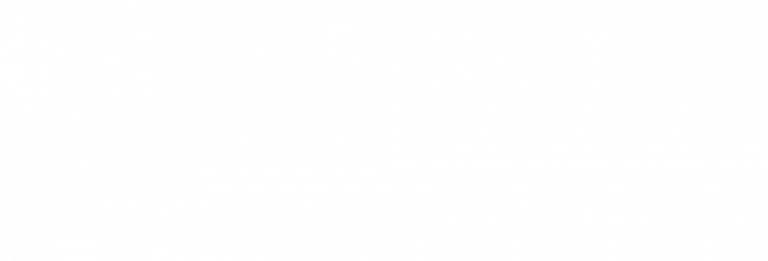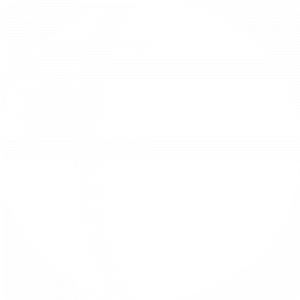在八月中前往美國之前,我待在終年受海風吹拂的臺灣島上二十餘年。從大學入學到研究所畢業後的那段期間,我住在臺北城裡,花了三分之一的人生摸索與搏鬥。和生活搏鬥,也和自己。有時候覺得已經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但是困惑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回來。所以無論何時,我總是在包包裡放著一把傘。既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放晴,什麼時候會下雨,那麼確保能在雨滴落下時打傘撐著,總是不那麼狼狽一些。
只是風總還是從四面八方灌進來。東北季風、颱風、冷風、西南風。偶爾讓人神清氣爽,但多數時候讓人直打冷顫。臺北的風如此,家鄉也是。小時候出門前,媽媽總會在我的脖子圍上一圈領巾,說是這樣能夠保護氣管,接著就讓我跨上摩托車的前座,載著我四處征戰,逆風經過小鎮上全都往同一邊傾斜的行道樹,去學校、補習班,去市場,去公園。那是臺中一個靠海的小鎮,在那裡,你必須學著與海風共處。風四處流動,在臺中,在臺北。來到美國更發現,逆著風走在任何城市的任一條路時,這種觸覺的記憶,都會被召喚過來。家的記憶觸手可及。
感恩節假期是來美國後的第一個長假。美國人在這段期間返鄉,和家人過節,我則飛離了波士頓,降落在中西部的芝加哥,準備和在俄亥俄州讀博士的好朋友Claire會合。飛機降落時從窗口眺望,那是我所看過最井然有序的夜景,燈火如棋盤一般工整。都會區的大眾運輸系統非常便捷,讓初來乍到的我安心不少,我幾乎確定未來幾天的旅程會非常順利。這是我對全美第三大城的第一印象:繁華都市、交通發達、人口眾多──無一和家鄉吻合,除了吹得放肆的風。
當天晚上我到了Claire的同學Karie的妹妹Kelsey家中,迎接我的是親切的主人、舒服的沙發床,以及一隻名為Pushkin的貓。Karie原本打算在同一天回芝加哥過節,順道載Claire來和我會合,但後來因故往後延了一天,便提議我先到的這天去Kelsey家過夜。我和她們素未謀面,所以在此之前問了朋友不下十次:「妳確定這樣不會太打擾她們?」朋友則耐心地再三回答:「不會,她們很熱情。」
當我發現陌生人們的善意是用這樣直接而毫不拐彎的方式展現時,總是懷疑卻又感激。一開始總是想參透為什麼,後來覺得這種思考不但沒有意義,也讓自己顯得彆扭。「在不太熟的朋友家借住是很常見的事情嗎?」「對他們來說好像很稀鬆平常,出門在外嘛。」「真的嗎?」「真的。」「人家都說沒問題了,所以就沒問題。」「他們會不會是不好意思拒絕?」「不會,美國人很直接的。」
Claire說Karie告訴她,深受基督教文化影響的人很願意做這樣的事情,這不是她第一次幫助不認識的人。我認識一個曾經去過臺灣學中文的美國朋友,他曾經認真比較過基督教與佛、道教的不同,意外地發現,不管虔誠不虔誠,受到基督教文化影響的美國人,多少都有「我做這件事情是為他人好」的想法。「臺灣人也很善良,也會為他人著想」,他說,「只是美國人會這樣想多半和宗教有關。」
這種東西方大相逕庭的直接/含蓄、交友習慣、宗教信仰,都是文化差異的不同面向,也構成生活的各個切片。有些時候來不及反應,但回過頭來想想,其實很有意思。究竟這些美國朋友的說法具有多大代表性,我並不確定,但這畢竟是一種解讀方式。而我也就放心地在Kelsey家住下一晚了──就像我所認識的歐洲背包客朋友們一樣,大方地進門,問好、握手,開心地離開,道別、擁抱。
Karie也邀請我們在感恩節當天去她的朋友家吃晚餐,所以我很幸運地吃了非常道地的美國感恩節大餐:烤火雞、馬鈴薯泥、南瓜派、蘋果派、烤布丁、烤蔬菜、紅酒配起司。之前在美國的超市看過用超大桶子裝的火雞醃料,覺得很誇張,當我見到餐桌上的食物份量,立刻想起了超市那些讓人匪夷所思的商品規模。到底是商品影響了人們的習慣,還是人們的習慣造就了商品的巨大化呢?Karie和朋友說,感恩節就是這樣,「先吃第一輪,飽了就和朋友聊天休息一下下,再回來吃第二輪,飽了就喝喝酒,準備吃第三輪,不用客氣,盡情地撕開那隻火雞的腿吧!」餐桌上的火雞只被吃了不到四分之一,據說剩下的肉是未來幾個星期的三明治食材。我想起臺灣的農曆新年。
雖然美國人並不是每天都準備這麼過量的食物來吃,但是平日生活中的飲食份量、消費習慣,似乎也不是太含蓄。我最無法適應的便是美國食物的份量以及不用環保餐具的習慣──學生餐廳提供吃到飽的各式食物、校園以外的餐廳少有確實回收的店家、超市販賣的產品容量常常大到超乎想像。這些現象背後反應了極端的消費主義和資本主義,問題非常明顯,但顯然沒有什麼有效的解決方法。提倡環保或適量消費可能違背人們長久以來的習慣,更可能打壞既得利益者的如意算盤。
再說,在一個龐大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很多時候人們想躲也躲不了。大財團或蓋戲院,或買球隊,或辦遊行,用各種非傳統的方式廣告,刺激消費,商品化各種口號與象徵,甚至將商品再商品化(比方把原本拇指小的巧克力做成手掌大小的巧克力,成為一種新的、具有刺激消費潛力的「新商品」),身處其中的人們常常防不勝防,一不小心就成了高度消費主義的共犯。黑色星期五更是如此。我聽過不止一個美國同學說他們很討厭黑色星期五,人們像發瘋似的。但不可否認,在電視廣告、網路促銷、降價銷售的誘因下,身處美國的人,不論在地人或觀光客,多多少少會在吃完不尋常的大量食物後,再瘋狂地隨著人群花大把鈔票買進大批商品。
上回我和一位美國教授聊天時,談到聖誕節的全球化與商品化,教授有些慨嘆地說,「這些節日都變得很商業,失去了它們原本的意義,美國人太瘋狂了,我身為美國人,為這種大概連臺灣也有的奇怪現象道歉。」我在他說完這段話後捧腹大笑,但也明白這種現象是任誰也無法輕易扭轉的僵局,笑完的同時感到有些無力。
感恩節的「傳統」與「精神」其實也是另一個僵局。當你將美國印地安人所遭受的待遇,對比各種關於這個節日的「偉大敘述」,會發現這是一個再讓人尷尬不過的慶典。不過在餐桌上沒有人討論這個話題。
新認識的美國朋友很友善地和我們天南地北地亂聊。招待我們的主人夫婦都在讀博士班,在座有一位劇場演員,另一位是大學講師。我們討論美國與臺灣食物的不同,爭辯到底是藍起司比較臭,還是臭豆腐比較臭。「臭豆腐這道菜的名稱也太可怕了,聽起來就很臭!」我和Claire聽了都笑了。我也發現主人的小孩雖然走路搖搖晃晃的,但已經會自己拿餐具吃東西了,這在臺灣是很少見的;通常臺灣的父母親會追著自己的小孩跑,把飯送進小孩的嘴裡,拜託小孩聽話乖乖吃飯。以前就聽說過美國父母與小孩相處的平等互重,不過這是第一次親眼見識。
劇場演員在離開前邀請我們隔天晚上去看他的喜劇演出。他說,「在紐約,每個人年輕的時候都得寫一本書;在芝加哥,我們不寫書,我們搞劇團。」我在隔天拿著通行證到櫃臺,可惜表演太受歡迎,已經沒有位置了。不過能夠看見黑色星期五的這天,售票口仍有這麼多人看表演,覺得非常特別。這種對表演藝術的熱度,是許多臺灣表演工作者的夢想吧。
看戲不成,在回到密西根大道與朋友會合的路上看到了另一場「表演」。新聞與氣象主播在大片玻璃櫥窗前面播報新聞,群眾聚集在櫥窗的另一邊欣賞。播報內容不是重點,重點是這種展示性強烈的姿勢(gesture)。我在紐約旅遊時也見過《早安美國》在時代廣場附近的直播,群眾一樣是圍著主持人與來賓,隨著導播的指示揮手或尖叫。工作人員的手勢和攝影機的鏡頭,大概能讓觀眾產生自己也是表演者的想像,因此觀看本身成為一種似乎能左右表演的動態參與,觀眾於是被吸引到攝影機旁與櫥窗外部,想像自己不只是靜態的被動的局外人。
在到芝加哥之前,我最期待的景點是博物館,除此之外沒有太大的想法,因為我並不是一個那樣喜歡都市的人。但是我發現芝加哥擁有的魅力比我預期的還要更大。密西根大道上有亮麗的商場,也有靜謐的教堂。這個城市裡有像芝加哥藝術學院那樣擁有豐富藝術館藏的博物館,也有極具教育意涵且設計細膩的科學與工業博物館。芝加哥河岸樹立著極具指標的當代建築和摩天大樓,密西根湖畔吹著未曾改變過的冷風。芝加哥有時候像是一個住著新靈魂的老城市,有時卻像一個歇著老靈魂的新都會。
我在感恩節到了一個不是家的地方,但是卻也過的自在坦然。冷風吹向臉上的時候,我想著,這和那傍水的小鎮上終年吹著的風倒也有幾分相似。雖然美國法官在數年前認定芝加哥之所以被稱為「風城」的原因,其實和風無關,而是因為過去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曾經在肉品市場、棒球賽事上與芝加哥互槓,而謔稱芝加哥為「風城」,暗指芝加哥人很愛吹牛;不過我想,我對芝加哥意外的好感,或許和它從湖上夾帶水氣而來的強勁寒風有關。朋友就算戴著毛帽都被吹得頭發疼,我這個來自海邊的孩子就算沒戴帽子,也安然無事。記憶中的風城,也就是這個樣子。
Chun-Wei Tsai holds a BA in English and an M.A. in Theater and Drama. She is a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er in Taiwan, and is interested in designing theatrical activities for language learning. She is now a Fulbright FLTA at Bosto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