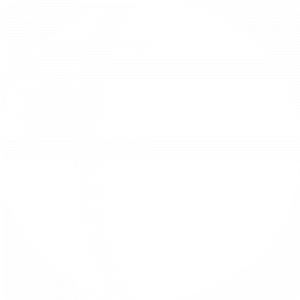摘要
環境和生態危機的克服,需要的不只是知識和技術,還需要信念、規範和實踐,並將人類與物種和自然重新連結。啟蒙以來的現代化思維獨尊人類主體性,割裂人與自然世界整體之關聯。中國哲學和東方宗教不具此一主客分立、獨尊人類主體(主宰性)的特性。而原住民傳統宗教和文化更不把環境和自然只視為人類可運用、可宰制的資源,而是肯定其為人類的來源或根源。中國哲學,儒、釋、道都具備完整的宇宙論和倫理學,並具實踐特性,重力行,又對東方文化影響甚鉅。故宗教生態學會將之視為重要資產,藉以探討其對永續生態的可能貢獻。
宗教生態學在台灣雖不普遍,但台灣具相當基礎與實力。本文以中文撰寫,目的在於拋磚引玉。盼學界及各界能多有著力,在此一課題上做出生態永續的全球性貢獻。
背景
生態與環境的危機已是全球性的共同難題。快速的工業化、自然資源的濫採和濫用、過度的消費、經濟模式的偏頗、分配的不公義、自我中心和意識型態的高舉、以及暴增的人口等,都是環環相扣的,造成人類和其他物種賴以生存的環境和生態出現災難的原因。此一災難性的課題,也是跨學科、跨領域共同關注並尋求出路的挑戰。在不同的理論中,有一些共同的訝異。例如: 科技和科學將把人類文明帶往何處,現代化的美麗願景而今安在,世界和人類的未來如何 (Grim & Tucker, 2014; Norgaard, 2002; Watling, 2009)?
宗教生態學的發展
環境和生態的危機並非單由科學和科技即可處理,還涉及價值、信念、社會制度、經濟模式、分配正義、生存型態和生活方式等面向。對於此危機的理解、處理和克服,有一整合式的趨勢: 即跨領域、跨學科的回到人類和物種賴以生存的整體環境,地球和宇宙。探討的不只是現象(災難)的處理與對治,還探究其源由。在此一發展趨勢中,宗教也是一股被重視,以及推動此一趨勢的重要力量來源。
自廿世紀末起,有不少來自科學、經濟、公共政策和宗教研究背景的學者,共同致力於此一課題的探討和處理,強調對話、合作及夥伴關係。1992年5月,有150位美國的神學家和科學家齊聚華府,為環境尋求出路。其論述基礎在於,科學和宗教的結合,能為地球環境危機的處理,做出根本性的重大貢獻 (Norgaard, 2002)。哈佛大學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在1996到1998年間辦理了系列的跨領域會議(分為10個部分)。此一整合性工作,在1998年10月,聯合國所舉辦的宗教與生態論壇 (Forum on Religion and Ecology) 達到高峯 (Grim & Tucker, 2014)。會議中決定要繼續在哈佛所推動的工作,而後有關宗教與生態的出版持續增加,國際組織陸續成立或擴充。宗教與生態論壇移到耶魯大學,耶魯大學「森林暨環境學院」和「神學院」也共同設立「宗教與生態」的研究所。耶魯大學結合科學和宗教的課程 Journey of the Universe,其教材獲得 Emmy Award 2012。普林斯頓大學在1994年強化其原有的環境研究,進一步設立跨領域的環境研究所,從事教學、研究和推廣的工作。早在1991年人文即被納入其環境研究,在2000至2006年間更設立環境人文中心。哈佛大學環境中心雖以科學和科技探討為主軸,近年也強調與人文的跨域合作。
啟蒙傳統的迷思和限制
生態和環境危機並非突發事件,而是現代化發展的一個不幸的結果。當代文明的傲人成果,如民主和科學,其發展源頭可上推至啟蒙運動,甚或文藝復興和古希臘時期。這是一個突顯理性、強調人的主體性、與啟示和神權做區隔,進而以人為世界中心的思想源流。在此一智性源流中牛頓開啟了機械性的世界觀,以自然為同質性的物質,依照可預測的律則運作 (Watling, 2009)。經由17世紀科學的興盛,18世紀的啟蒙運動,19世紀的工業革命,20世紀的科技發展和全球化,以至於發展出強勢的現代性或啟蒙的思維模式與心態 (Ibid.)。
這是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將世界對象化,並以機械性的模式認識世界。強調理性的優位性,以及科技和經濟的進步。認為人的理性可以探求和證成真理,也是真理的標準。人依靠理性可以認識世界(和自我),運用世界資源。科學和科技是建設人間世的最佳憑藉,世界只是可用的資源。自然也被經濟性的理解成商品,可管理、可使用 (Ibid.)。人作為世界的主宰,對此世界人可以無止盡的開採和運用,以及濫用和破壞自然。
啟蒙運動以來,西方思潮及文化所建立的是人自身的絕對的主體性,主體的自由是一種解放的自由,不受羈絆的自由,其內容是自主決定。在社會、政治和經濟面向,獨立的個體是這些活動的最終基礎。人可自由的追求自我的人生目標,並自主的與他人建立社會和契約。即以影響迄今的洛克的基本人權為例,生命、自由和私有財產都只是對人而言。私有財產最根本的正當性來自人對這世界的勞力付出,世界是豐富的資源待人開採運用,人自己賦予自己主宰世界的特權。雖然基本人權的根據可上推至天(上帝),而有所謂的天賦人權,但在獨尊人類主體和理性,以及貶抑宗教教義,或以人為中心來解釋宗教信仰後,也去除了人對世界和其他物種的道德責任和適當關係的指引。天賦人權雖然是用以保障每一個體,但也是人凌駕於世界的特權。民主政治發展至今,雖已是世界的主流,但也只限於具主體性的人類,具一定條件的人,例如公民 (Schmitt, 1988)。廿世紀末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羅爾士,其正義原則是處理政治社會資源分配的最基本原則(Rawls, 1971, 1993),其影響迄今而不隧。但其公平、正義並不及於符合一定條件的人以外的物種和世界,也只是保護人對世界的特權。
此一獨尊人類主體(主宰)的思維型態,雖源自古希臘,卻在啟蒙運動時期開啟了高峯。另一與之相對的,被啟蒙理性所排除及貶抑的宗教(一神論),竟也是建立人為世界中心及主宰的決定性因素。Lynn White (1967) 即論述,基督教信仰使得科學和科技與自然相對立。在創世紀中明載,只有人是依上帝的形象所造,被賦予管理這世界的使命與職責。人也分享了上帝與世界的區隔,以及對被造物的控制 (Norgaard, 2002)。亦即,源自古希臘的理性傳統和希伯來的一神論傳統,都型塑了人為世界中心及主宰的思維和存在方式。不只西方學界有此反省,中國哲學界的前輩如牟宗三(1983),即論述此一東西文化的根源性差異。
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所謂的進步和幸福,是由工業生產和消費以及物質來測量 (Watling, 2009)。因著人的優位性,以及快速發展的科學及科技的助益下,追求成長和進步的同時,卻也罔顧其對環境的嚴重破壞(Norgaard, 2006)。不只是對生態的破壞,還包括對異文化的侵略和殖民,以及區域間的不公義。例如強勢國家和財團於開發中國家掠取資源,卻將被破壞的生態和環境以及廢棄物留在當地。經濟發展和生態的保護間存在對立和衝突 (Norgaard, 2006)。然而,地球是一整體,這些區域性的生態及環境惡化,終究呈現出全球的生態及環境危機。
面對環境和生態的危機時,即或有來自於各領域的努力,以試圖減緩或防止持續惡化。但啟蒙以來的理性思維,缺少對人以外的物種和自然界的整全的理解和道德義務。在以人為中心 (Anthropocentric)、人凌駕於物、人的利益計算為主的思維模式下,人對自然的破壞並不意外,環境和生態的持續惡化也不偶然 (Dawe & Ryan, 2003; Norgaard, 2006; Rosenau, 2003; Watling, 2009)。雖然一直有來自於科學、科技和實務界對於環境和生態的危機做出的回應與修正,但單只是對啟蒙以來的現代化發展做修正,尚不足以理解和處理環境和生態的危機。需要的是重塑對自然的態度、理解和共存方式。人對於自然環境須有存在性的投注,個人和社會的轉變,以及新的價值和方向 (Watling, 2009)。例如深度生態學即以生態為中心,論述生態具有自身內在的價值,將人置於更廣的範圍架構下,強調相互依存的動態關係。面對當代的環境和生態危機,需要新的母體,新的生態道路,新的生態道德,和生活方式。面對此一危機和挑戰,宗教能提供道德的架構和敘述,說明人與環境的互動,並帶出實踐。
中國哲學對宗教生態學的可能貢獻
在近廿年宗教生態學的發展中,中國哲學和東方宗教益受重視。哲學包括宇宙論、倫理學、自然哲學等,論述或規範人與自然的關係。其內容包括概念及理論的建構,以及實踐的規範和應用。宗教包括敘述、論證、符號、儀式、制度、結構、群體規範和生活方式等。宗教不只是理論,更是實踐、規範和信念。每個文化均有其宗教所傳講的生命故事,解釋天地萬物 (Berry, 1999),也連結人、宇宙、自然、社群和物種,並具體實踐於文化中。
啟蒙以來的現代化思維割裂人與自然世界之整體關聯,中國哲學和東方宗教不具此一主客分立、獨尊人類主體(主宰性)的特性。而原住民傳統宗教和文化更不把環境和自然只視為人類可運用、可宰制的資源,而是以之為人類的來源或根源 (Grim & Tucker, 2014)。環境和生態危機的克服,需要的不只是知識和技術,還需要信念、規範和實踐,並將人類與物種和自然重新連結。若缺少了信念、規範和實踐的改變(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倫理規範和生存方式等),人仍可能只是修正宰制世界的方式和技術,卻仍然破壞世界。信念、規範和實踐的反省和修補,正是宗教可貢獻之處。例如中國哲學,儒、釋、道都具備完整的宇宙論和倫理學,並具實踐特性,重力行。加上其對東方文化的影響(生活方式、生存型態和信念),故西方宗教生態學會把中國哲學、東方宗教和原住民傳統文化置於宗教的範疇理解下。視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資產,藉以探討其對永續生態的可能貢獻。
例如中國儒家民胞物與的核心理念,格致修齊治平的人格發展典範,以民為本卻非獨尊人類。中國哲學一如杜維明(1996)所言,世俗生活也是宇宙秩序、天道天性的實現。中國哲學所著重的經世濟民,是符應人對宇宙天地參贊化育的道德義務,而非宰制世界。張載,西蒙也論到:天為父,地為母,眾生為兄姊,萬物為同伴。宇宙為我身,天理為我性。人存在的終極意義在於實現天道天理,參贊天地之化育,而非將人的個別(偏私)意志置入宇宙。人與萬物均源自於自然,世界非外在的物,而是人實現及完成自我的所在之處(家),人且具有護持天地萬物的道德責任。這些都是中國哲學對環境和生態危機可貢獻之精髓所在。
挑戰
然而在目前的宗教生態學領域中,中國哲學和東方宗教卻也面臨下列幾個問題和挑戰:
1、西方的誤解:西方對中國哲學的理解或有疏誤和偏頗,卻會被根基已朽的華人視為圭臬。例如於加拿大設立宗教及生態研究中心的James Miller即把道家和道教混為一談,而中共官方的中國道家(教)協會卻疏於檢視還與之唱和。在宗教生態學的領域,台灣學界可有對世界更多的貢獻。
2、核心價值、終極關懷的被忽視:中國哲學對人、人世、人所處的宇宙天地均有關懷與責任承擔。然因西學至上,當代中國哲學界也重知識。專研學術之際,核心價值、終極關懷反而易被忽視。而社會處境也加速其邊緣化,實踐特性被漠視,也失去了對時代的引導。如何將中國哲學經世濟民、參贊天地化育的理念與社會實踐結合,是一大挑戰。
3、文化延續發展的挑戰,對人類文明的可能貢獻:民主政治保障個體平等、自由,卻無以擴及至人以外的存在,也無以護持宇宙天地的永續發展。民主反倒保障了人對世界的特權,以及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盛行,而科學和科技更加速其發展。當代環境生態的危機,可謂是民主和科學高度發展的結果。當環境和生態危機暴露了民主和科學的限制之際,中國哲學(尤其儒學)以天、地、人為一體的內聖外王傳統,能否補民主之不足,並防止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盛行,及其所造成的環境和生態危機?中國哲學對於人類文明和宇宙天地的存續發展能否有所貢獻?這不只是中國哲學自身的存續發展之問題,也是中國哲學能否對當代課題(生態永續)做出貢獻的挑戰,這是否是中國哲學在當代的承擔與使命?
English Topic:
“Chinese philosophy, eastern religion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 new topics on Contemporary Religious Ecology”
English Summary:
To tackle the crisi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logy, the author believes we need not only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worldviews,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to reconnect humans, other species, and nature.
Modern thinking from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focuses on human subjectivity, which is disconnected from the world of nature. Chinese and eastern philosophy does not have this subject-object separation, or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human subjectivity/mastery. Aboriginal religion, in particular, sees nature as the origin of human beings, instead of resources that can be controlled or distributed. Chinese philosophy, including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all have well-rounded systems of cosmology and ethics. They are all practice-oriented and influential in the eastern culture. Therefore, the Forum on Religion and Ecology at Yale sees the eastern religion as an important asset, encouraging more dialogues around it for its potential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ecology.
Religious Ecology is not yet popular in Taiwan, but has a great potential for growth.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in Chinese with the hope of reaching Taiwan’s academic society or wider audiences and generating meaningful contributions around the world.
References
牟宗三(2015) ‧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台灣學生書店
杜維明(1996). Beyond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0(1), 58-75
Berry, T. (1999). The Great Work: Our Way into the Future. New York: Bell Tower.
Grim, J. & Tucker, M. (2014). Ecology and Religion.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Norgaard, R. B., (2002) Can Science and Religion Better Save Nature Together?
BioScience, 52(9).
Norgaard, R. B., (2006)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post-Brundtland world, Ecological Economics, 57, p.253–268.
Lynn White Jr., (1967)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3767:1203–1207.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wls, J. (1993).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osenau, J. (2003)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bleak prospects for sustainability.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3, 11– 29.
Schmitt, C. (1988)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Translated by Ellen Kenned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Watling, T. (2009) Ecological Imaginations in the World Religions.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