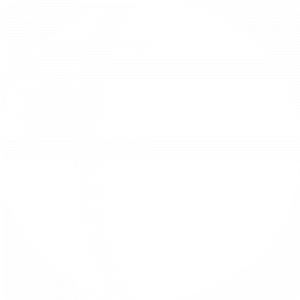打開學術視野與交流體驗-UCSF
抵達美國,先是參與由愛達荷大學(University of Idaho)主辦,為期五天四夜的Gateway Orientation Program。接待人員舉著傅爾布萊特的立牌在機場裡迎接學員們,由機場驅車前往愛達荷大學,歷時約2小時的車程。

抵達美國,先是參與由愛達荷大學(University of Idaho)主辦,為期五天四夜的Gateway Orientation Program。接待人員舉著傅爾布萊特的立牌在機場裡迎接學員們,由機場驅車前往愛達荷大學,歷時約2小時的車程。

Summary of work Researchers and educators consider CPS as one of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the 21st century. However, students often fail to solve a

Conside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my teaching career a chapter book, to be able to come to America and learn again seems to be the

這半年期間,本人曾多次參與美國傅爾布萊特基金會所舉辦的大小活動,而與在美國的傅爾布萊特學人有所交流,同時本人也在UCLA旁聽幾門相關的課程,並出席幾次專題演講與討論會,另外,還去美西的博物館與圖書館訪查與本人研究相關的文物收藏與資料。除了從事研究工作以外,本人想分享兩次寶貴的經驗,以饗大家。

CHAPTER 1 Where I Am From I am TzuChun Lin, a 2019-2020 FLTA grant fromTaiwan. I started my magical journey at Georgia Southern University as

既榮幸又幸運能獲得Fulbright獎學金,讓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在工作與進修多年後,有機會於2018年8月到2019年7月到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擔任訪問學者

Preface The modern history of Taiwan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Dutch period (1624-1662), the kingdom of Cheng period (1662-1683), the Qing Dynasty

很榮幸獲得2019-2020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助,來到加州小鎮Davis,於UC Davis進行十個月的訪學。

I am grateful for the funding and support that the Fulbright Program offers me. Also, writing this reflective essay provides m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但問起一般美國人對北卡的印象,仍舊與傳統南方、菸草與棉花緊緊連在一起。曾經是美國棉花帶(Cotton Belt)的一部分,直到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北卡州內的36萬的美國黑奴才獲得自由。蓄奴制度與南方邦聯(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的歷史緊緊糾纏,直到現在跟美國的朋友談話,南方邦聯仍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點。